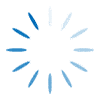上一次步履这般匆忙跨进祈年殿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出现在白榆视野中时,贺景珩已坐在椅上服药。
余光看见人来,他似是一直盼着,立马抬眼看去,恰是所念之人,立马喜笑颜开,放下了本打算举碗一饮而尽的汤药。
“陛下...呃...”太监正不明所以,想要阻拦他又远离口边的手,顺着他点目光见到来人便明了,将劝话咽回了肚里,揖身退至一边。
白榆看见他被折磨得有些虚弱的模样,也没什么要说的了,径直在他旁边拉开凳子坐下。
贺景珩观察着她的眼色,以指腹将药碗一点一点推至她面前。
她并未表现出其他反应,淡淡瞥了一眼,便端起碗拿过大监递来的勺,舀起汤药送给他。
白榆的视线虽落在他嘴上,却并不真切地直直穿过,眼波渐渐涣散开。
她本想同他商量,这三宫六院他既连见都不见,平白在此蹉跎年华,何不尝一纸诏书放了意在自由之人,于他于她们,岂不都是一桩美事。可一来并非所有人都厌倦深宫,对高贵身份和不必付出就得来的富贵终是留恋,二来说是遣散,若要让天子与这许多人和离,那又是莫大的损辱。
而这些终究是小,最重一条,是她总会有离去的一日。
她无神的目光不由上行,停于他的眉宇间。
放她们自由,便昭示着余生,只有她于他身侧相依相惜。可若连她都不在了...
无论他对她的眷恋能延续多久,无论他是否真正此生非她不可,这对于贺景珩来说,都无异于沉重的背叛。
白榆的手无意识来回动作着,她的思绪却丝毫不在这碗中渐消的药里。
可只要宫中还留有人气儿,待她绝情之时,他会否并不那般孤独呢。
她又一次收回被喝空的勺子,却不防被贺景珩忽的抓住手腕拉回了脸旁。
白榆这才遽然回神,身子也跟着往前倾了些,害怕碗里汤药会洒,忙稳住身体低头看去,才发觉原来早已见了底。
她飞快眨了眨眼,想要隐去愈发藏不住的愁绪,抬眸看向他,可令她怔愣,对方的眼里已许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眼神。
他眉头低压,眼尾微挑,叫习惯了温情的她蓦然看见这般危险的双目,犹如与猛兽共处到忘其本性的猎物,登时失了阵脚。
他掌心的手小幅颤了颤,被尽数感知到。
而贺景珩也在将她的慌张收入眼中后,也不着痕迹地柔和了下来,双唇在她掌心轻轻一印。
“在想什么?”
“在想,你以后还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我就再也不管你了。”
他笑起来,又拉着她的手去摸自己的额头,“你瞧,一点儿都不烫。”
白榆赌气似的抽回手,看向一边,“昨晚说了多少次今早有寒流,紫宸宫是没你的衣物还是怎的,愣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
贺景珩油盐不进,丝毫不为所动,圈过她的腰把人提溜到了腿上,双手不安分地开始在她身前逡巡。
“温柔乡里睡一夜,谁要还能记起来其他的,我才是真佩服。”
“你...”
贺景珩却突然失了力一般迷离起来,打断了她的话,“头有点昏昏沉沉的。”
“...”
“陪我歇一觉吧。”他埋头与她肩上,气息也变得凝重起来。
白榆无奈答应了他,牵着他走至榻前,宽衣解带。
只着里衣相贴,她才感觉到背后的温度实是灼热,方才竟被他额上散开的温度骗了过去。
可屋外北风呼啸,能躲在如此暖意里也是在令人舒心。
白榆闭上眼,往圈揽着自己的怀抱里又挤了挤,闭上眼决定先不再思那些烦心事。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