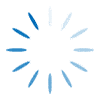山林悄寂无声,黑云压顶,风——
……
风雨反正是来不了了。
有也得憋回去。
卜宁看看师弟,又看看师父。尘不到显然没想到会从门里拽出个这么小的,表情极为罕见地空白了一瞬。
他没说话,神色间透着一种复杂的微愕感。良久后,他牵着人的手轻动了一下。
“怎么又长回去了……”
他自语似的叹了一句,然后弯下腰,看着那双猫似的眼睛。
那双眼睛的瞳仁圆而乌黑,清晰地映着他的影子。他看了一会儿,放低了嗓音问:“还认得我么。”
那一小团就那样看着他,紧抿着没什么血色的嘴唇,一动不动。
乍一看依然像无声的对峙。
但慢慢的,那双眼睛沿着边缘一点点泛了红,却还是极倔地一眨不眨。
又是良久,安静中响起了一声:“尘不到。”
那一刻卜宁长长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便发现尘不到的肩线居然也松了下来,长发从那里滑落,半遮了脸。
从他的角度看不到师父的表情。
他只听见尘不到温温沉沉应了一声,将面前的人抱起来说:“这里寒气重,先回家。”
***
这次的无相门开在陇西,距离宁州刚巧三千多里。
普通人行车需要十多个小时,阵门一开,就只用一壶茶的功夫。
尘不到走在阵门长而漆黑的通道里,听见怀里那一团说:“我能走。”
通道很安静,隐约能听见后面卜宁、夏樵他们模糊的人语。尘不到袍摆轻扫过黑暗,脚步没停,也没把他放下,说:“这么点腿就算了吧”
不知道是觉察到了尘不到直到现在也没笑过,还是别的什么。以往闻时听到这种话,必然要说点什么或是做点什么回敬回去——就像当年往尘不到面前拎小王八。
这次却没吭声。
他就趴在尘不到肩上,老实得几乎算得上温顺。
尘不到走了一会儿,忽然问道:“还记得多少事?”
趴在肩上的人闷着,像是快睡着了。过了好久才咕哝似的回答道:“都记得。”
其实尘不到知道。
从看见那双眼睛、听见那句“尘不到”起,他就知道闻时什么都记得。
他从无相门里牵出来的还是那个人,完完整整,一点都没有丢。只是身体出了点状况,需要从头来过。
但他还是又问了一遍,像一种确认。
“无相门里的呢,都记得么。”尘不到又开了口。
怀里的人僵了一下。
“无相门里难捱么?”尘不到问。
“……不难捱。”
闻时静默了几秒,又道:“没什么难捱,睡一觉的事。”
尘不到抱着他走了很长一段,才再次开口:“所以你觉得哪怕多走几遍也无所谓,是么?”
“因为等你出来了,就可以骗我说没什么难捱的,不过是睡一觉的事。你这是笃定我进不了无相门,没法知道门里什么样?”
“我要是问你天谴加身、尘缘埋尽是什么滋味,你是不是也要跟我说一句没什么难捱,睡一觉的事?”
“闻时,谁教你的办法?”
即便是这样的话,尘不到也是一字一句缓声说的。只是语调很沉,落在阵门的黑暗里,将间隙中的安静衬得更加旷寂。
就好像连虚空都噤声不敢语。
闻时没吭气。
过了不知多久,尘不到感觉怀里那一团动了一下,闷不作声地搂住了他的脖子。就像小时候从来又倔又硬,唯独做了莽撞事又不知怎么开口时,会忽然软化一下。
尘不到:“……”
他一手养大的人,什么脾气他可太清楚了。要是闻时顶着成年模样站在这儿,必然会犟着或是撅回来,拉不下这个脸。
也就仗着这会儿有个没他腿高的唬人模样。
尘不到简直气笑了。
他真的在嗓子里模糊笑了一声。阵门里一片漆黑,所以没人能看到他的表情。即便有人看见,也不一定能体会到那种冗杂难明的后怕。
“等你恢复原样了我再跟你好好算这个账。”
“……”
这下怀里那个是真不吭气了。
***
相比于他们这边,落后一段距离的卜宁、夏樵和张碧灵就松快许多。
起初卜宁其实十分担心。
他虽然满腹书卷,懂的也杂。但无相门已经超出了他既有的认知,所有了解都来自于闻时的寥寥描述。
这是他第一次真实地见到无相门,也是第一次接到从无相门里出来的人。他差点以为闻时一忘皆空,要全部重来了。
还好有夏樵。
小樵实操经验为零,但架不住有个接过闻时两次的爷爷。
“以前听爷爷说过,我哥刚从无相门里出来的时候,确实都是小孩儿模样。”夏樵解释。
“其他呢?其他会受影响么?”张碧灵问,“像他刚刚的模样,也就四五岁吧?他是只记得四五岁时候的人和事,还是都记得?”
“唔——”夏樵回想了一下,“我想想爷爷那时候怎么说的。好像是说刚出无相门的时候,我哥总会有点反应不过来,可能还没脱离门里的感觉吧。但缓过来了就什么都记得了。”
“那他这模样会持续多久?”卜宁最为担心的就是这点,“须得从头长起么?”
夏樵连忙道:“不用不用,很快的。”
他想起沈桥留给他的日记:“1921年那次他接我哥,见到人的时候就已经是十多岁的样子了,没走多远就恢复原样了。还有,我见到他的那次也是,从将军山坐车到我家也就四十来分钟吧,反正他到我面前的时候,就是正常样子。”
夏樵大致算了算:“怎么也超不过一小时,快的话说不定半小时就行。”
“就是半个时辰或者两刻。”周煦突然冒头来了这么一句。
夏樵才反应过来卜宁老祖不这么计时。
“哦。”卜宁放了心,“那就好。”
“老祖别担心。”夏樵又补了一句,“等到从这个阵门里出去,就可以看见变化了。少说也能长到十几岁。”
小樵话放得很满。
结果当他们真的从阵门另一头落地,就看见尘不到抱着胳膊倚着衣柜,床上是夏樵那个缩了水的哥。
他盘坐在那,不声不响地盯着面前深灰色的床单布,留给众人(主要是尘不到)一个乌黑的发顶。
夏樵缓缓冒出一串问号。
“这不还是四五岁吗?!”周煦第一个没憋住,也不敢乱说话,只狠狠捅了一下夏樵的腰眼。
小樵“噗”地漏了气,“昂”了一声。
“你昂什么啊?”周煦小声往外挤着话,“不是说分分钟长回去?你家分钟按最短的针算啊?”
“你问我我问谁?”夏樵也很懵。
他眨巴眨巴眼,小声叫了一句:“哥?”
床上那位参禅的抬了一下眼,朝他看过来。乌黑的眼珠蒙了一层浅色的光,凉飕飕的。
夏樵缩了一下:“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这迷你款的哥显然不太乐意说话,盯视了他好一会儿,才蹦了一句:“有点问题,暂时长不回去。”
“什么问题?”
“不知道。”
夏樵“唔”了一声。
之前在无相门外他们情绪太重,没太注意。现在一听,他哥这声音也有一点退回去了……
虽然不太夸张,但以他哥那个脾气,也挺要命的。
怪不得不乐意开口。
夏樵不敢触霉头,没再跟他说话。而是扭头朝这里最大的那位看去,用口型询问:“祖师爷,我哥真的碰到麻烦没法变大啦?”
尘不到没转眼,眸光依然落在床上那祖宗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夏樵总感觉祖师爷的表情很……意味深长。有种“我就听着你编”的意思。
过了片刻,尘不到“嗯”了一声,道:“是变不了,挺麻烦的。”
夏樵听见“麻烦”两个字就有点慌:“那怎么办?”
尘不到:“泡药。”
闻时:“?”
他瞪着尘不到还没开口,夏樵那个二百五已经被带着跑了。
“泡药?”夏樵想起以前煮来给闻时泡手的那种,立刻道:“那我去厨房把上次那个砂钵找出来。”
尘不到:“砂钵小了点,装不下你哥。”
闻时:“??”
夏樵:“噢,那用什么?”
“用浴桶——”尘不到顿了一下,切换到了现在人最常说的:“——浴缸,这情况只泡手没什么作用,哪里不长泡哪里。”
夏樵:“……头呢?”
尘不到:“一起泡了吧,匀称,有人从小怕丑。”
闻时:“???”
“那药……”
“楼上都有,一会儿让老毛找齐了。”
“老……”
老毛?
可是老毛已经不在了啊。
众人听到这话,均是一愣,尤其是张碧灵。
都知道金翅大鹏鸟老毛是尘不到的傀。尘不到一旦恢复了,傀也能跟着重见天日。可即便如此,也得先用傀线——
张碧灵疑问还没出口,就反应过来……
是了,祖师爷尘不到捏傀根本不用傀线。
她刚明白这一点,楼上就有了动静。
那是一道并不算重的脚步声,因为懒得抬脚的缘故,在地板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张碧灵听过这样的脚步声,夏樵更是熟悉。
老毛每次在西屏园上下楼梯,或是在沈家别墅二楼房间往来,就会有这样并不吵闹的动静。
其实按理说,傀想要做到无声无息很容易。这样的脚步声反而才是刻意的——为了不吓到人,为了更有活气更像生灵。
而只有长年累月的刻意,才会形成这种像人一样有特点的脚步声。
张碧灵听着那道脚步,一时间想不明白,跟着祖师爷尘不到的傀,为什么要练这种动静。
没等她想明白,夏樵已经一溜烟跑出了屋。
“老毛叔?!”他站在一楼客厅,勾着脖子朝二楼张望。
“别叫唤,听见了,我拿药呢。”一道声音从楼上传来。
真的是老毛!
夏樵看见一道人影落在二楼扶手上,从左边房间移到了右边房间,有什么东西被搁下了。
下一秒,他就听见了扑翅声。
一个枭鹰似的影子从二楼直掠下来,从他眼前横飞而过,斜扫进房间。翅羽扇子似的张开,隐隐流动着金色。
它在屋里盘旋一圈,稳稳落在闻时肩头。
一如当年在松云山的每一天。
它用并不动听的声音说道:“一般来说,躯壳长不大是因为体质太虚、灵神太弱,支撑不了——”
老毛说到一半,鸟眼一瞥,瞥见了闻时的手指。
这祖宗的迷你手指头上还有不知哪天缠绕的傀线,带着残留的血迹。傀线这种东西最能反映傀师的潜意识和灵神强弱。越虚弱,傀线越僵。反之越强,傀线就越灵活。
而闻时的傀线就像有生命一样,正不屈抖动着,试图张牙舞爪地窜出去。只是还没来得及窜,就被闻时默默摁住了。
这是一场无声的斗争。
老毛位置得天独厚,刚巧把闻时的小动作尽收眼底,没说完的话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
灵神弱个鸟。
这骗术也就哄哄大傻子。
老毛再也不分析了,用毫无起伏的语调和嘎嘎的鸟嗓说:“药找好了,泡你的澡去吧——”
吓唬谁呢!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