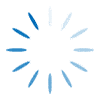见得对面人长相,韩若海最后那半分困意也被惊得飞到了九霄云外,心中忍不住暗叫一声不好。
原来这从人名唤许逢,本是韩家一名老仆的儿子,自小聪明灵活,又会来事,很得韩若海叔父韩令看中,虽是还叫他在家中伺候,却早做过承诺,如若其人能考上,便会资助他去书院进学参加科考。
那人往日常在韩叔父身边服侍笔墨,比不得幕僚、管事,然则人人都高看他一眼。
韩若海犹记得自己刚来京城的时候,小堂弟考入了白马书院,婶娘想叫这许逢去送读,不过一两日功夫而已,却被叔父一口拒绝,说书房里头有事,轻易离不得。
这样一个人,眼下竟是给送来顾府伺候自己作息,给婶娘晓得了,嘴巴上头不说,不晓得心里会憋屈成什么样。
韩若海自入京以来,因他才高能干,常被叔父拿来同两个儿子比较,衬得二人一无是处。
他颇通人情,察言观色,看出婶婶面上客气,细微处却难免带出些难受,偏两家又是至亲,叔、婶皆是长辈,又避让不得,只好小心留意。
谁料想一觉起来,竟是见得面前站着这样一个大麻烦,一不留神,韩若海差点将脖子扭了,口中忙道:“怎的叫你来了?”
那许逢连忙上得前来,一面给他递衣裳,一面恭敬道:“官人吩咐小人过来小心伺候,特叫小的同七少爷说,休沐足有三日,家中并无什么要紧事,不着急催你回去,客随主便,自听主人家安排便是。”
如果说先前韩若海只觉得麻烦,此时听得这样一番话,则是变为了诧异。
这回休沐之前,因韩若海早答应了顾简思,叔父得知后,还特地叫人给他带话,说近日因顾侍郎事,吏部很是惹眼,叫他去同窗家坐一坐就走,莫要多言多事,径直回府便是。
怎的一觉起来,又变成“不着急催你回去”、“客随主便”了?
这变化实在太大,韩若海一时有些适应不过来。
那许逢又道:“官人还说,若是便宜,七少爷不妨也邀这一位小少爷来府上做客——难得同窗,实是缘分,当要多多走动……”
话已是说到了这个份上,如果说韩若海还未察觉出什么不对来,便是真傻了。
他一肚子话想要问,偏偏碍于顾家的随从就在一旁,还跟着一齐伺候洗漱,实在不好多说,又因误了时辰,匆匆收拾妥当之后,照着指引,急忙去小书房寻人。
***
灵寿韩家积蕴百年,韩若海又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少时便跟着长辈外出拜访,见识过的书房不知凡几。
然而看到顾简思的小书房的时候,他还是吃了一惊。
说是小书房,房间却是大得很,还未进门,便见顶头一方匾额,两边挂着对联,上书“满将正气参天地,必留丹青照古今”。
字写得很是寻常,也无半点落款,可其中内容口气,却是叫人看出了一身冷汗。
这话怎的能胡乱说?还能这般堂而皇之地挂在书房门口,让往来人全数看进眼里!
韩若海此时心中已经开始打鼓,却又觉得以自己了解,简思并不是这样狂妄之人,至于昨日见的顾父、顾母,更是半点不张扬,绝不会不知分寸。
他思绪微乱,等到进得房内,其中并未挂字挂画,也无什么摆设装饰,当先入眼的便是两墙书柜,满满当当摆着书,除却寻常经义,最惹人注意的是正中间的一个柜子。
当中成排成列,最上面三四架的书脊上只写了《手札》二字,又排有一二三四,最后数到一共四十五册,中间的架子也有两排,书脊上是《小记》二字,排了有二十一本。
无论《手札》也好《小记》也罢,上头俱是没有署名。
韩若海压下狐疑之心,先朝正站在桌案前顾简思打了个招呼,复才羞愧地道:“我起得晚了,顾叔叔说的寅时……你怎的不给人叫我!”
顾简思笑道:“我娘特地吩咐的,说好容易旬考过了,平日里必是没能睡好觉,难得今次休沐,让我们睡足了再起来。”
韩若海的眉毛都失望得垂了下来,面上的神色甚是复杂。
简思的娘亲实在是体贴,这一觉确实也睡得极舒服——整一个月里头,只有今日早间醒来没有从前那疲惫感,只觉得许久没有这样精力充沛过。
可比起睡个好觉,他也想多腾出一点时间来,听简思的父亲说话。
想是看出了他的心思,顾简思递了一叠纸页过来,道:“我爹今日有事,只同我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他特给你留了书信……”
韩若海忙不迭接过,立时就拆得开来。
那书信虽然是代写,却很长,当先夸他文章做得好,立意很正,开题也开得准,夸完之后,便开始给他改文。
改文用的是新纸,并非在原稿上。韩若海的文章才千言出头,可这一份如何改文的书信就足有两页。当中不但提点了他用的典故不够妥帖,言语过于含糊这些个细处,还特帮着调整了结构。
韩若海照着调整后的文章在心中过了一遍,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同样一篇文章,不过换一个切题的点,调整一回前后,又按着书信中说的或将长句改为短句、胼句,或将结语改为单句,简直是焕然一新,此时虽未写得出来,只在心中品砸,竟是也给他品出了几分大家手笔的味道在。
韩若海又惊又喜,继续往下看,却见其中点出了自己一处错误的释义。
他眉头微皱,心中想了又想,虽是认为顾叔叔不会出错,一时却也不清楚自己哪里错了,便抬头问道:“简思,你这一处有没有大柳先生注的《隆平集》。”
顾简思随手指着当中的书架道:“你去翻那一处的《手札》,八、九、十三册便是注的《隆平集》”
韩若海并无他想,依言去了,然则才把第八册抽得出来,便吓了一跳。
书的扉页就盖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红印,上书“柳伯山印”四个字。
再往后翻,有涂有改,往往一处地方,有三四个不同的注义。
韩若海学问做得扎实,一眼就辨认出来自己在课上学的是哪一个,可另外几个版本,却从未听说过。
他越看越是心惊。
韩家到底是书香世家,虽然与柳伯山来往不多,可也藏有其人少量书画,另还有难得的中堂,全数被小心收得起来。
韩若海这样出身的小孩,父母却并不怎的出挑,少时靠的全是自己。他只有遇得大考考好了,才能借机壮着胆子求大人把大柳先生亲手写的文章原稿借出来临摹仿写,对这一位大儒的笔迹十分熟悉。
此时他抱着手里的书,不知怎的,心中忽然生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倒吸了一口凉气,叫道:“简思!”
顾简思手中提着笔还在写字,听得后头叫,回头问道:“怎么了?找不到吗?”
韩若海努力叫自己镇定些,勉强笑着问道:“这书上头盖了大柳先生的印,字也极像,不会是谁人仿着他的笔迹手书罢?”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